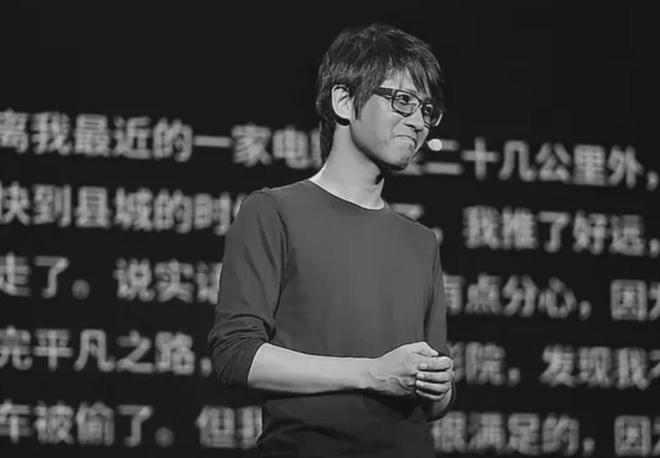IPP评论是国家高端智库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(IPP)官方微信平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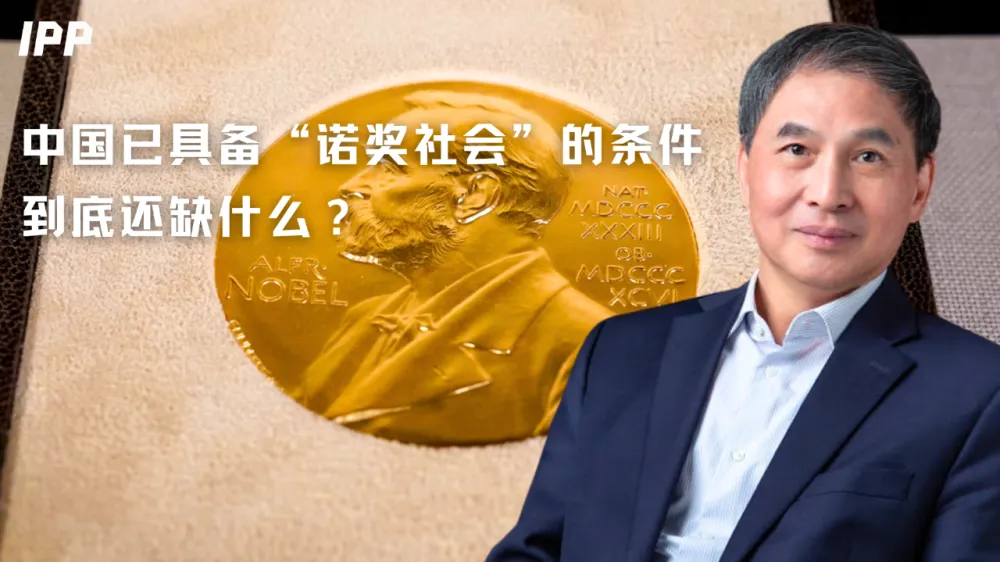

郑永年:中国很多方面已具备“诺奖社会”的条件,还有何短板?
如今,无论在科研投入、人才规模,还是成果产出与前沿突破方面,中国都已实现了质的飞跃。然而,每到诺奖季,我们仍常陷入擦肩而过的“躁动”中。
诚然,诺贝尔奖并非衡量国家科研实力的唯一标准,但长期以来,它偏向那些能够突破人类认知边界的研究,这类突破往往需要几十年的验证与积累,许多获奖成果对后世科研产生了深远影响,其中不乏华裔、日裔学者的贡献。若仅以“政治性”或直觉质疑诺贝尔奖的含金量,似乎有失偏颇。
跳出情绪化的表达,中国已经拥有庞大的科研体量以及门类齐全的科研体系,为什么总与诺奖有“一步之遥”?
在郑永年教授看来,从许多指标来看,中国完全具有“诺奖社会”的条件。但诺奖青睐的基础研究,尤为需要研究者带着纯粹的好奇心探索,但当下我国存在 “帽子”“级别” 等形式的诱惑、行政化的干扰,以及“有组织科研” 对个人兴趣的压抑,都在消磨这份纯粹。另外还有来自功利主义的教育与文化土壤的更深层次问题。

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于10月8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。图源:新华社
郑永年教授认为,如果仅从指标来看,中国社会确实具备了“诺奖社会”的条件:学界和知识界的生活水平已超越中产水平;我国有世界级的学术和科研基础设施投入;在一些学科(例如医药)中,学者拥有巨量的样本;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,学者们拥有很大的自由度;中国的研究产出量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,已成为“论文大国”。
因此,人们需要进一步从环境与土壤两个方面思考。诺贝尔奖强调的是原创性的研究和发现,而应用性研究则很难获得奖项。基础研究需要具备一些条件:一是研究者独一无二的兴趣,二是研究人员所拥有的自由,三是研究者们所享有的经费保障。从这些方面来检视中国学者所处的环境,就能看到一些现实问题:
第一是“帽子”。中国的“帽子”具有巨大的含金量,学者常为争取一顶“帽子”花费巨大的精力。
第二是“级别”。中国学界各领域常被各种“学阀”所控制。知识界的竞争基本上表现为学阀之间的竞争。一个学阀一旦消失,往往会出现“树倒猢狲散”的局面,难以实现传承和积累。
第三是“位置”。中国学界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行政主导的体制。若能获得位置,“屁股指挥脑袋”的原则就开始发挥作用 ,学者一旦变成“官员”,往往会荒废研究。
第四是“荣誉”。在极其势利和功利的环境中,如果无法带来实质利益,荣誉便毫无价值。学者们对自己荣誉的不尊重与社会对学者荣誉的轻视互相强化,容易形成恶性循环。
第五是“有组织科研”。研究者们的兴趣往往需要服从于组织或国家的“兴趣”。同时,“有组织科研”大多带有服务于“赶超”目标的应用性质,而且也往往导致思想市场的缺失。
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功利主义的教育与文化土壤。迄今的教育秩序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“人”,而是培养“才”。这个“才”在前期由家长和老师等广义上的“组织”决定。而进入现代社会后,教育系统更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有效工具,学生必须实现国家的“兴趣”。对各个层面的权力载体(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)来说,培养人才就像生产“土豆”一样。这种局面的延续对学生、家庭、社会和国家都是不利的,更不用说实现人们摘得诺奖的目标了。
文章链接
中国的诺贝尔奖“躁动”|独思录 x 郑永年

郑永年:中国—东盟共同市场一旦形成,能迸发多大价值?
如今,东盟已有效取代美国,成为中国最大的区域出口市场。2024年,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占比为16.4%,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份额。今年前三季度,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6.6%,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。
目前,中国—东盟自贸区3.0版谈判也已全面完成,3.0版新增内容涵盖数字经济、绿色经济、供应链互通等新兴领域,具有开创性意义。中国—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拓宽。有分析指出,若东南亚地区能进一步加强内部整合,新组成的供应链将为区域内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创造巨大的空间。
郑永年教授近日在接受《中国东盟报道》专访时指出,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制造业基础非常强大。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共同市场,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市场,都有望实现成倍增长。

10月16日,2025中国-东盟海洋产业合作发展圆桌会在福州召开。会上举行了中国-东盟海洋产业合作联盟、中国-东盟海产品交易所、闽江海外发展服务中心启动仪式。图源:央视网
目前,东盟的角色正从“世界工厂”向“世界市场”转变。郑永年教授认为,“工厂”和“市场”并不矛盾。他以英美“脱实向虚”导致产业空心化为鉴,阐明强大的制造业是市场的物质基础。如今,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制造业非常强大。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共同市场,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市场,都能实现成倍增长。
面对外部冲击,美国要求东盟国家不要与中国做生意,尽管其目标是本国的再工业化,但这种政策无助于东盟发展,甚至可能导致其“去工业化”。因此,强化中国—东盟合作对双方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。
在文明与价值观层面,东盟体现了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,践行“和而不同”。其“共识政治”模式比西方多数决制度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。儒家文化与各宗教在东南亚的融合良好。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实际上是全方位的,我们共享着同一套亚洲价值观和亚洲文明。
在战略应对方面,郑教授提出中国应实行“单边开放”。这是中国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好的公共产品,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西方某些势力的逆全球化力量。相较于拜登政府的多线围堵,特朗普上台可能反而减轻对华战略压力。
关于中国叙事的构建,郑永年教授强调,需避免过度强调特殊性。在构建中国叙事时,一定要与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。过度强调特殊性而忽视普遍性,会使人难以接受。
详细报道
中国东盟报道|郑永年:建设中国—东盟共同市场 塑造亚洲世纪新格局

郑永年:中国经济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
在近日举办的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公共政策学院“对话院长”研讨会第二期上,郑永年教授就中国公共政策与经济发展发表了看法。
他认为,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“内卷”,郑永年教授给出了他的“改革三支箭”:宽松的金融环境、积极的财政政策,以及尤为关键的“松规松绑”。
他指出,过度监管正抑制着新质生产力的涌现,唯有在技术落地与产业准入上大胆放开,才能打破内卷困局,避免创新成果再度流失。

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、120万亿元、130万亿元,今年预计可以达到140万亿元左右;过去4年,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均5.5%的增长速度。图源:新华社
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,郑永年教授表示,如果一定要做三件事,我选择这三件,也就是中国的“改革三支箭”:
第一是宽松的金融,
第二是积极的财政,
第三是“松规松绑”。
当前经济内卷严重,价格不断压低,总量呈现收缩趋势。例如,咖啡从20元降至2元即是缩影。内卷本质是对存量市场的争夺,一旦新赛道出现便迅速拥挤,如低空经济。若能释放更多赛道——包括新质生产力与各类新技术——便可打开局面。问题是监管过度,发展不足。
以游艇产业为例,我国海岸线漫长、造船能力领先,却因监管限制未能充分开放。同样,中国企业在创新药研发中贡献全球约20%成果,却因审批周期长、风险资本缺位、医保控价严等问题,导致许多成果低价流向海外。
三支箭中“松规松绑”尤为重要。具体而言,对环保、劳工权益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应严守红线、严格监管,但在技术落地和产业准入方面则应放宽限制,激发创新活力。正如特朗普和马斯克推动的“去监管”改革,如果我们不加快在关键领域松绑,很多技术成果将如创新药一般流失海外。
对地方政府也需适度松绑,在防腐败前提下,允许政策探索中存在容错空间,区分谋私腐败与执行偏差。
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
排版|刘昕冉 周浩锴
审校|刘 深
终审|刘金程